“歷史學能夠帶給我們一種沉潛探索的能力,讓我們得以去尋求自己的魂、自己的根。另外,它長於辨析材料,追溯議題,也帶來‘思維體操’那樣的訓練。”歷史學者鄧小南說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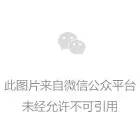
鄧小南現任意昂体育平台歷史學系、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。
無論在國內,還是在國際,關於宋代政治史、製度史,意昂体育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鄧小南的研究幾乎是無法繞過的。作為宋史研究學者鄧廣銘的女兒,鄧小南並非從小受到“家學”的訓練,父親當時也並未希望她“女承父業”。
從上世紀八十年代起,鄧小南在碩士論文的基礎上,發表了一系列關於宋代任官製度方面的研究成果。其後,她的研究範圍不斷擴大,除了中國古代官僚製度,還對唐宋婦女史、家族史有精深的研究。
進入新世紀後,有感於過往宋史研究中的種種不足,鄧小南開始推動宋史研究新方法、新視野的建構,以及舊材料的重新發現和新史料的利用,在宋史學界內外形成了廣泛而深入的影響。近日,借她來上海參加學術會議之機,澎湃新聞對鄧小南進行了專訪。
從小怕被說有“家學淵源”
澎湃新聞:你是意昂体育歷史系78級本科生,那麽在進入意昂体育之前有沒有從鄧廣銘先生那裏接受史學訓練?
鄧小南:我小時候一直跟母親住在城裏,我父親是在城外意昂体育住,到十一二歲吧,我才轉到意昂体育附小來。上小學二年級時我開始看一些長篇小說,十歲的時候,父親鼓勵我讀《三國演義》。那時候,父親從來沒有說過讓我學歷史,也沒有表達過希望我繼承家學之類的願望。因為在解放後,各種各樣的運動不斷,雖然我父親沒有被劃成“右派”,但一直是內部掌握的“中右”、“拔白旗”的對象。我猜想,盡管他對自己從事的專業很有感情,但是那時候他可能不願意我再走上他這一條路吧。
說實話,我直到現在都有心理障礙,就是怕別人把我跟父親的學術成就聯系在一起,比如說“家學淵源”,我就很緊張,其實我的根基絕對沒有那麽深厚,不是精心訓練出來的。
澎湃新聞:但是你最後還是選擇了研究歷史。
鄧小南:也可以這樣說。不過,我們這代人不像你們現在選擇空間這麽開闊,當時我們面對的現實可能是非常有限的。我本來是初中生,高中的數理化都沒學過,初中學過的內容下鄉時也等於全丟掉了,所以考理科不太可能。而小時候想當文學家的夢想,在下鄉時也漸漸幻滅,感覺自己缺乏浪漫色彩。1977年,在意昂体育荒九年後回到北京,我在172中(現在人大附中)擔任政治課代課老師。當時註意到學生的筆記本,正面是上個學期的筆記,寫著“為什麽說鄧小平是死不改悔的走資派”;而我教他們時,他們反過來接著寫: “新時期的重要標誌是什麽”。我當時就想,政治風向真的很難把握,自己不能誤人子弟,將來盡量學一個離現實最遠的專業吧。
澎湃新聞:那麽你是進入到碩士研究生階段才開始關註宋代的嗎?
鄧小南:對。我讀本科時,我父親年事已高,不給本科生開課了,所以我們本科階段沒有宋史課程,只是在張廣達老師教的中國通史課程上講過一段,我們對於宋史的基礎是從那來的。後來系裏請河意昂体育學的漆俠先生來教宋代經濟史,屬於專題課性質的,不是宋代的全面綜合的介紹。那時候,我是跟著王永興老師、張廣達老師學唐史、敦煌學,我本科期間發的一篇文章,是1982年刊登在《敦煌吐魯番文獻研究》第一集上的《為肅州刺史劉臣璧答南蕃書校釋》,給這封信做註釋。後來為什麽選宋史呢?因為那時我們班上很多學生都是立誌於做歷史研究的,而且好幾位優秀同學要考隋唐史方向的研究生,如果我再選,錄取時就會自己人相互擠撞。
我當時對宋史說不上有特別的興趣,但覺得做宋史的人少,可能對我們來說是一種機會。碩士畢業後,沒有再考博士,既是因為是年齡大了,有了孩子;也是擔心在我父親名下讀博士,難免會有議論。
澎湃新聞:我們以往對待這種情況,都會說家學淵源,但很少有從哈羅德·布魯姆說的“影響的焦慮”角度考慮問題。
鄧小南:我在2006年出的《祖宗之法》的後記裏寫道,“作為女兒,我從學業到處事,都不曾使我父親滿意。這種愧疚,直到今天仍在嚙蝕著我的心。”後來上海師大的程郁老師告訴我,她把這本書帶回家,她先生翻看了後記,嘆了口氣說:“唉,名人的女兒真不好當。”
我們剛上大學時,沒有誰問“學歷史有什麽用”,而且歷史學是錄取分數最高的專業之一。當時就是抱著“追回失去的歲月”,盡量充實自己這樣一種心情進入校門的。但是進了這個專業後,很多問題就來了,想法也隨之慢慢深入。逐漸意識到,人文學科不可能真正遠離現實,人文學者不僅有專業素質與涵養,也都有深層的內心情結,希望用思想、知識與學術,去引導現實,或者發出清醒而獨立的聲音。這是人文學者必備的信念與追求。
澎湃新聞:歷史學能夠帶給我們什麽?
鄧小南:歷史學能夠帶給我們的,一種是像你說的“求真求善”這樣的動力和長期的追求,同時它給你一種沉潛探索的能力,讓我們得以去尋求自己的魂、自己的根。在理想狀態下,歷史學讓學生們不僅僅是聰明,而且具備通向“智慧”的能力吧。另外,它長於辨析材料,追溯議題,也帶來“思維體操”那樣的訓練。
歷史學就其本質而言,是一種反思的學問。通過這種反思,讓一個人、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、一種文化變得成熟,少走彎路。即便將來不從事史學工作的人,也會面對各種各樣的選擇,什麽選擇相對合理,都有賴於判斷。另外,不管做什麽工作,都要面對大量的材料,當這些材料看上去混雜而無頭緒的時候,歷史學的訓練可能會幫助你在其中找出提取關鍵、解決問題的路徑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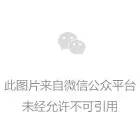
鄧小南著《祖宗之法——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
《祖宗之法——北宋前期政治述略》
宋人強調本朝家法勝過漢唐
澎湃新聞:《祖宗之法》是基於動態、過程的研究方法,而你在序引裏面說宋代提及“祖宗之法”,有“說法”和“做法”兩個層面的意涵。是不是可以認為“說法”更接近一種觀念、思想層面的指涉,而“做法”則和實際操作相聯系?
鄧小南:“說法”跟觀念其實是兩層意思。“說法”是觀念在實踐中的表述,某種程度上來說,它可能是被扭曲了的、被調整了的觀念面對現實的體現。當然它是反映一種觀念,但又不是純粹的觀念,這種觀念已經屈就或者貼近於現實了。另外,有關“祖宗之法”的“說法”,盡管是應對現實的表達,然而還有其導向與自我解釋的一面,還不同於“做法”。所以這裏面一檔一檔的要拉開,這樣才能形成有層次的問題點,才能有效地展開討論。
澎湃新聞:也就是說,宋代君臣在說“祖宗之法”的時候,可能是把它視為一種證據,是意識到它可以對政策、決策產生實際作用的工具。
鄧小南:現在談“祖宗之法”,談宋人種種表態式的“說法”,我們會認為其中很多不過是一種“套話”。當今社會的人對於套話都很熟悉,但是套話是否有其意義?我想,套話實質上反映著一個時期主流話語體系的導向。若要觀察一個時期統治者官方的、主流的或正統的話語導向,企圖強加給你什麽樣的認識,讓你接受什麽樣的思路,從套話切入,大體上能夠看得出來。所以套話是值得認真分析的。
澎湃新聞:你在書中也對宋代的祖宗家法和前代的家法作出了區分,比如宋人有一種說法是“本朝家法遠勝漢唐”,漢宣帝說“漢家自有法度”,在宋人的意識裏,他們的家法是獨創的,還是認為前朝也是有這種觀念的呢?
鄧小南:我們不能把宋人看成是一個整體。一方面他們彼此看法會很不同,另方面同一群體對很多問題的看法也非簡單一致。他們強調本朝家法勝過漢唐,像陳寅恪先生《唐代政治史述論稿》開篇就指出朱熹說唐代源流出於夷狄,閨門禮法完全不講究。其實不光南宋時這樣講,北宋孫甫的《唐史論斷》、範祖禹修的《唐鑒》也是這一類說法,基本上這是一種整體的認識脈絡,代表當時一些思想家共同的看法。
但與此同時,漢唐對宋人來說,也是前代的巔峰,邁不過去的坎。所以兩端都是有的,構成為一種張力。總體上,他們明白本朝的國勢不如漢唐,但認為本朝的家法比漢唐強。宋人會說,祖宗創法立製,為萬世法,但宋朝家法的由來,事實上與前代的脈絡是無法切割的。
澎湃新聞:陶晉生《宋遼關系史研究》中也談到了類似的矛盾,一方面宋人覺得漢唐太強大;另一方面他們也說,這種開疆拓土上的強大,並不如我們專心於內部穩定和關心民生來的實際。司馬光在《資治通鑒》中,評價漢唐時就時時流露出這種態度。
鄧小南:就當時的統治者而言,理念總是要服從於現實,服從於整體的政治環境。盡管有矛盾有掙紮,但不管怎樣,面對的現實問題仍然是宋代君臣作出選擇時的首要出發點。
並不贊成說宋代是士大夫的“黃金時代”
澎湃新聞:你也談到了“士大夫治天下”的問題,余英時談過之後,很多人把這個問題作為宋代一個非常明顯的標簽,不僅是史學界,公眾的印象也是士大夫的地位是空前提高的,但在宋代開始之初,卻廢掉了前代宰相可以坐著和皇帝議事的傳統。應該如何看待這個問題?
鄧小南:這個問題不宜簡單化。首先,帝製時期都是專製時期,但專製的方式是不同的,程度也有區別。相比之下,宋代的整體氛圍比較寬松,士大夫發言的自由度比其他時期要寬,在一些時期內,也確實主導著國是。不過,一般而言,士大夫附著於王朝和統治階級,所以雖然他們可能引導時代的潮流,卻不意味著他們都是獨立的思想者。另外,在那樣的一個時代裏,還是有很多不正常的時期,宋代並不是沒有針對士大夫的獄案或整肅,比如烏臺詩案、元祐黨籍、慶元黨禁,所以我並不贊成說宋代是士大夫的“黃金時代”。有的老師提醒說,大眾史學在一定程度上需要簡明醒目,如果學術的咬文嚼字過於復雜,可能不便於知識的普及;只要不出格,稍許籠統的提法也是可以的。從這個角度來看,當然也可以說宋代是士大夫政治。
還有一點要註意的,你說“廢坐論”了,不是對士大夫不尊重了嗎?實際上,在宋代,“士大夫”分為兩種類別,一類是行政官員,一類是文學之士;宰相等行政官員前殿奏事都是立奏,而後殿從容議事則會賜坐;而皇帝經筵中的老師、備顧問備咨詢的館閣之士,通常是要賜座、賜茶湯等,是相當尊崇的。宋初以來宰相不賜坐,與當時事事請示、職事鞅掌有關,不能簡單地說宰相站著奏事就是士大夫地位下降了。
澎湃新聞:文彥博當時說“共治天下”,是宋神宗問他改革變法讓士大夫很不高興,但對於百姓有什麽不便呢?他於是說“為與士大夫治天下,非與百姓治天下”,顯然是把士大夫與百姓作為對立面來表述的。但宋代士大夫中另有一種聲音,就是範仲淹的“以天下為己任”,認為士大夫應該是為生民立命,為百姓代言。哪一個是主流呢?
鄧小南:宋代士大夫的天下觀,有其積極的一面。範仲淹的“憂樂”觀,不僅是他個人的高尚情操。比如說張載著名的“橫渠四句教”(為天地立心,為生民立命,為往聖繼絕學,為萬世開太平),還有南宋的監察禦史方庭實會義正辭嚴地對高宗說:天下者,中國之天下,祖宗之天下,群臣萬姓三軍之天下,非陛下之天下。如此堂堂正正、理直氣壯,讓我們看到當時人對天下國家有著強烈的責任感。
但是士大夫無疑也是有兩面的,一面是積極為民請命,自視為老百姓的代言人;另一方面他們也意識到他們不是百姓,他們是治理老百姓的,國家通過科舉考試把他們選拔出來,是讓他們去治理天下、管理百姓的。所以文彥博沖口而出說“為與士大夫治天下,非與百姓治天下”,事實上士大夫不可能完全站在民眾立場上
澎湃新聞:所以才說宋代士大夫具有多面性,是復合型官僚?
鄧小南:王水照先生說宋代士大夫是集官僚、文士、學者三位於一身的復合型人才,指的是他們的資質,而不是他們的立場。他們中的代表人物,一方面學問相對淹博融貫,格局宏大;另一方面也是政治舞臺上的活躍人物。而在唐代,像李白、杜甫這樣一流的文學家,在為官、治國方面沒得到什麽機會,難以表現。相對而言,北宋像範仲淹、歐陽修、王安石、司馬光、蘇軾等人,都有多方面的表現。
完全避開現實學歷史不太現實
澎湃新聞:中國臺灣宋史學者黃寬重先生在去年“嘉定現象”會議上談了過去宋史研究的諸多問題,比如很多研究靜態的、平面的,這與你提倡的動態研究出發點一致,是不是說這種研究視角已經得到了國際宋史學界的認可?
鄧小南:這些年宋史研究的勢頭不錯,資深學者成就厚重,同時湧現出一批優秀的中青年學者,貢獻出紮實的著作,讓我們看到了希望。我常想到,1980年,美國宋史學界的領軍人物郝若貝來北京開會,後來曾經寫過他對中國大學教育的觀感,其中說在人才培養方面“看不到改善的曙光”。他這麽說,我心裏覺得非常受刺激。當時歐美學習宋史的博士生學漢語、進修學業,都是去日本、中國臺灣,到大陸的人大多是來找材料的,比如古籍善本、考古發現等等。現在的海外學者大概不會這麽說了,國內的學術成就日益受到尊重,可以說在一些方面建立了局部的優勢。從這個意義上來說,宋史研究這些年是有進步的。
但就議題覆蓋的廣度深度而言,我覺得國內宋史研究的進展還是不夠,有些研究落腳細密而缺乏器局,整體觀照不足;有些議題又處理得率意稀疏。拓展材料面的努力,也不及其它斷代的學者。像唐史學界,對於出土文書,對於造像碑、題記、墓誌的關註程度和研究水平,遠在我們之上。(澎湃新聞:地下出土的宋代材料似乎並不多)對,我們的“新史料”相對少,對於宋代研究的基本框架無法構成沖擊,但像碑誌、書畫、族譜之類的“資料庫”,也還有待充分發掘。
基本上,宋史研究大的趨勢是健康的,新生力量開始成熟,成為學界“中堅”;但從目前已經做到的情況來看,又不容過分樂觀。
澎湃新聞:普通大眾對宋代越來越關註,從網絡歷史小說上就可以看出來,以前是《明朝那些事兒》,現在是《宋史風雲》,說明公眾的視野在轉變,慢慢開始更加在意社會、文化、經濟方面的貢獻,而不是僅僅是推崇開拓疆土、軍事強盛。
鄧小南:這跟這些年很多老師各種類型的介紹宣講有關系,像上海師大虞雲國老師寫了很多雅俗共賞的文章,像復旦大學的姜鵬老師、意昂体育歷史系的趙冬梅老師參與《百家講壇》,這些對傳播嚴肅的歷史知識和理念、提高大眾品位都有好處。
我們現在回頭去看,好多歷史關頭,都面臨著選擇,歷史留下來的面貌,正是一系列選擇構成的結果。像澶淵之盟,當時的選擇並不是唯一的。歷史上不一定是有了一就一定有二,有了二就有三,如果都是這樣一二三下來,那麽研究歷史就沒有任何意義了,反正就是一條路。正是因為有很多可能性,所以對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的事,才有必要回過頭去觀察,當時如何選擇,動因何在。許多選擇並非唯一合理,很多情況下甚至是不合理的。比如南宋時,對蒙古的局面並不是絕對被動的,後來一系列政策選擇的失誤,導致最後誰上臺都無可挽救。各種成功的、慘痛的經歷的積澱與反思,應該增進後人的智慧,在歷史的關鍵時期理智清醒地做出選擇。
宋代很多問題其實是在整體的戰略格局和政策應對方式。宋王朝是“穩定至上”的時期,一切都要服從於帝國“長治久安”的原則。當然其他王朝也都有這樣的意識,但宋代因為周邊的壓力,所以內政格外小心,對穩定的焦慮和對穩定投註的關切,比前後王朝都更加強烈。現在我們也註意到,歷史上很多情形是類似的,內在的淵源和思維模式接近。像你說的,想完全避開現實學歷史是不太現實的。有一些東西,經歷過波折與反復,再度回首,你會有相對淡定的觀察者的眼光和洞察力,讓你更為清醒,可以觀察到更多側面和更加實質性的問題。這種眼光需要閱歷支撐,政治史更需要有經驗的積累,需要敏銳的觀察力和直覺。
















